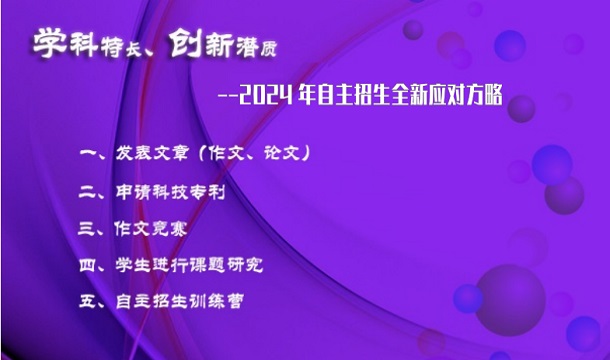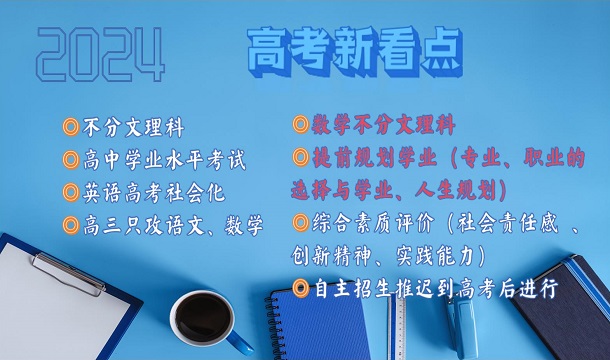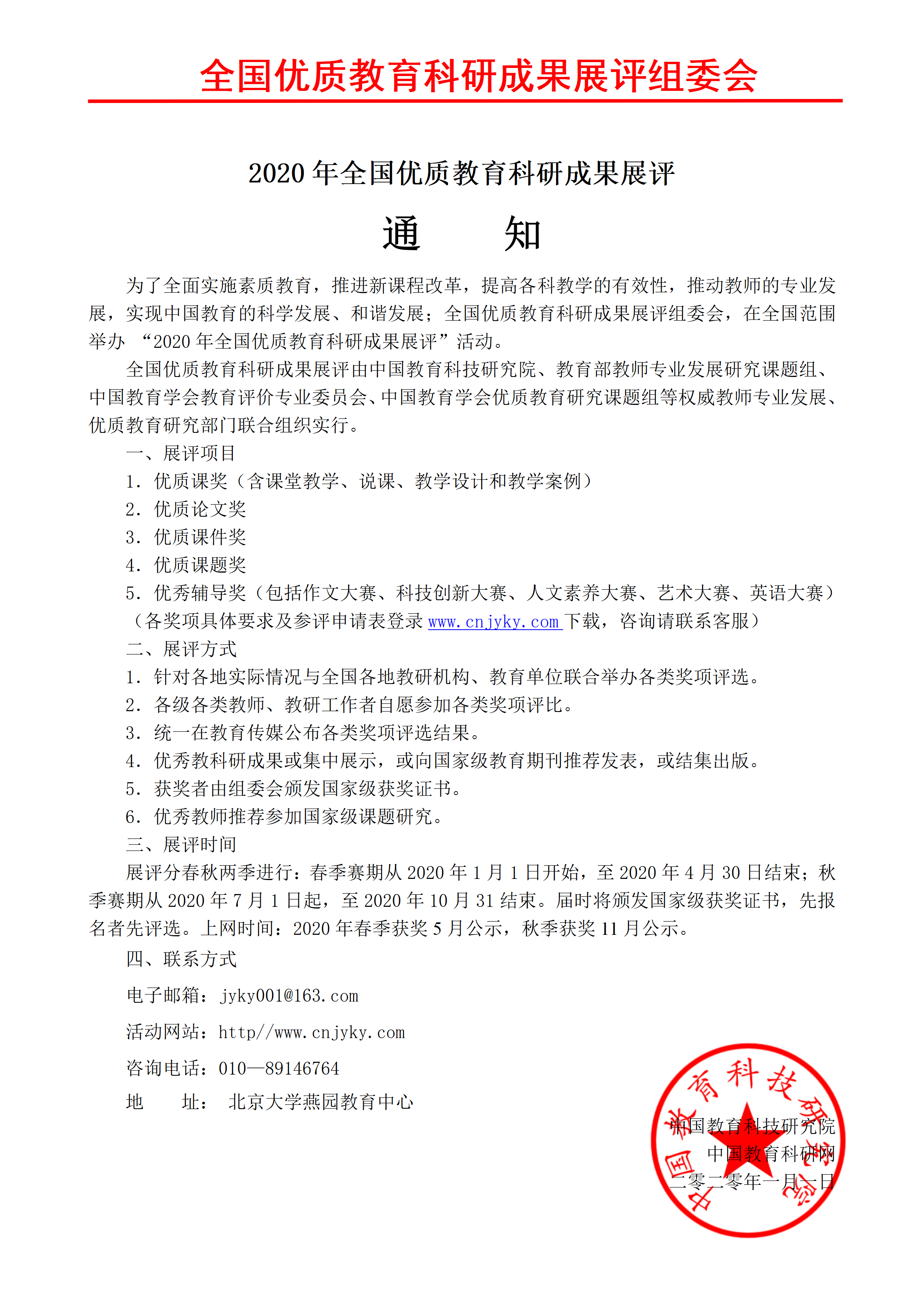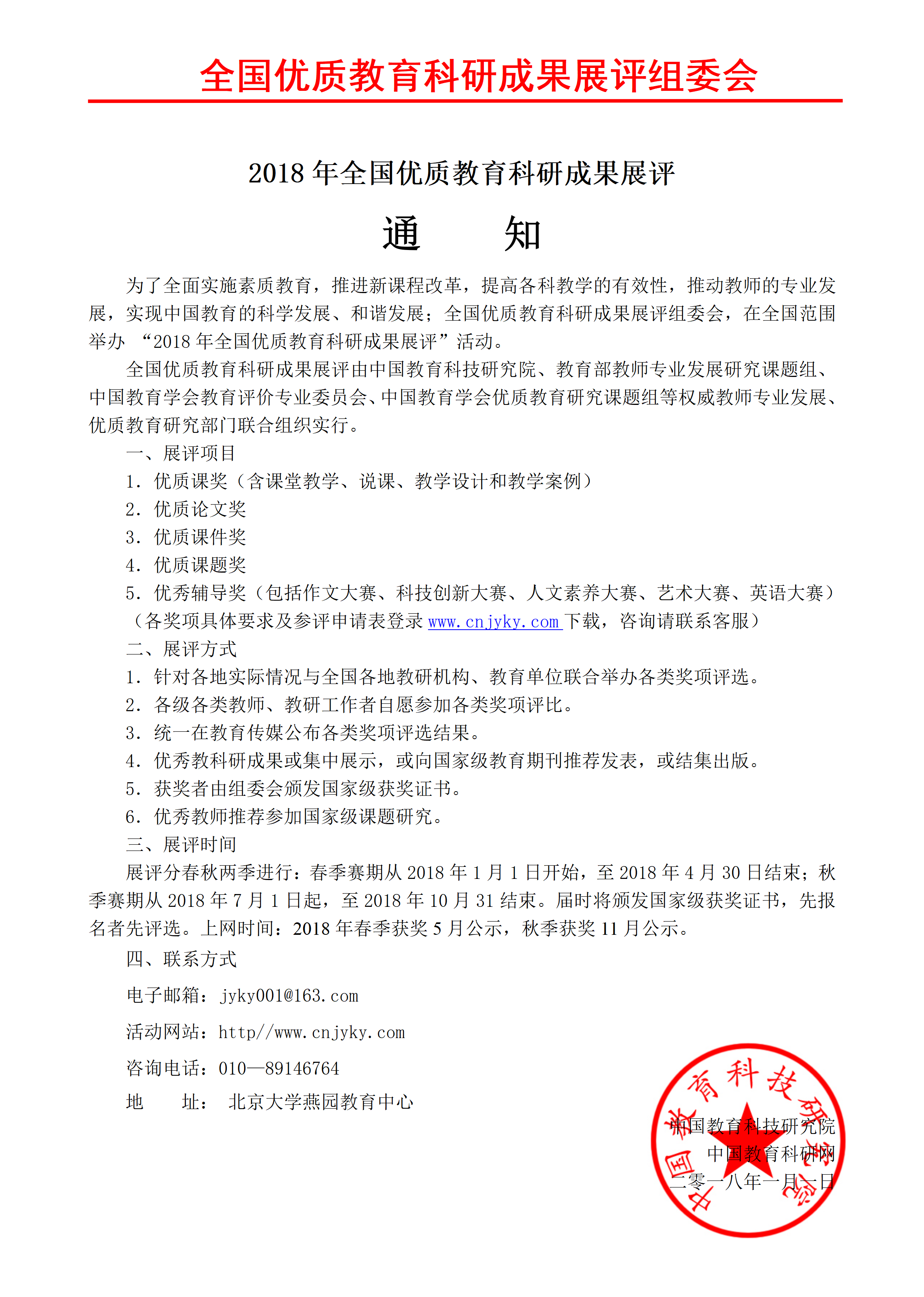| 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 |
| 时间:2016-10-12 来源: 周健 |
|
10月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发布会结束后,中国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这位记者问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机理”有何应用前景?吉拉斯面对这个有点“外行”的问题解释说“尽管在未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让人们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专注于应用。”急于“变现”的记者不会理解,也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科学认知和人文素养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毕竟,在中国,那些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最终一事无成的人,还经常遭到旁人的嘲笑。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中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中就认识到,一个有价值的行为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人类的社会伦理必须超越结果导向的简单驱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标,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 1949年,汤川秀树代表日本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以后的16年间,日本共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2000年以后,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开始上学的青少年。日本二战前和战后,教育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人当作“爱国工具”来培养,后者把人当作“人”来教育,把教育孩子什么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学生以亲身经历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科学家治学的不同,他说日本人的强项是努力和坚持,而美国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坚持、自由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的距离,是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的区别。 目前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共有九位华人,分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 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 2009年物理学奖)、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九位获奖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陆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后在大陆读过两年小学,其他人1949年后均没有在大陆接受过教育。 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华人也能获奖说明,华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没问题。但大陆人基数如此之大,为何获奖者只有屠呦呦一个“另类”?很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识”不教“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中国家长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投资就要选收益长见效快的专业,专业选准了,孩子就成人了;对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是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各种有用的“工具”,上个八十年代,这种行为被解释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晏阳初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张首先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希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至今没变。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经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很多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养活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看懂简单的宣传标语,能进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马也爱国”、能“为政府出力”就好,至于究竟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得不多。 蔡洋,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有理由,就是支持”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仔细观察,大量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有真理,只有立场。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学课程中“排它性”政治教育的结果,简单固化的价值观,教育的出来的人大多偏执而缺少包容,对待异己分子不共戴天,对同胞下手比对动物还狠,这教育,对“和谐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对方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手足无措。 因为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留在它国爱中国。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长估计也想不明白。 仁和义是“人性”教育中的两个基础。所谓仁,就是要宽宏大量,要有气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谓义,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着应对,而不是覆雨翻云,见利忘义。 教育中缺少了“仁义”二字,自然就会种瓜得豆。 半夜还没睡觉,你老婆问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而在为公益项目写文案。 “为了文案能够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为什么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捐钱。” “你们收那么多善款要干什么?” “我们机构才会有影响力。” “影响力有什么用呢?” “就才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资” “拿更多的工资,我们就可以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幼儿园。”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性”,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外在的、别人设定的目标行动,而不是为人自身在行动。人本身成为了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人,不是考虑什么事情能不能干成,而是考虑这个事情自己是否愿意干,自己愿意怎么干。后者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当成目标来对待,而不是台上谦谦君子,台下相互利用。 做公益需要筹款,你是用“脏钱”去套腾讯的钱呢,还是打“泪点”忽悠老百姓捐钱,还是,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随缘。这三种办法,虽然拿回来的钱是一样的,但拿钱回来的人却大不一样。 对于前两种募款的办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密尔也不敢这么干,因为那么做,从长远看会降低次生效益,会损害社会对公益组织的看法,会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愿。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于赚快钱的中国人对此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术和规则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钱搞到手。 公益是件严肃而专业的事情,即便是募款,也要考虑很多细节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秦晖说中国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统,教育也是如此。以专教人学些吃饭、养家糊口本事的职业教育,把“学以致用”当指南,以“仓廪实、衣食足”为里子,以“知礼节、知荣辱”为面子。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手段,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讲“有钱”以后,该怎么做“人”。从职业中学毕业,会点化学知识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里加,把豆制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肠里加,只管自己赚钱,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关的礼节和荣辱教育,特别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夺不餍”的“狼性”当做职业精神来培养。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读书一知半解,便以为世界的机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来国家社会江湖商业非以此为准不可,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当空中楼阁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维码的时候,以国家为己任的丰满理想立刻瘪变为与有权有势者同流合污,狗苟蝇营。 同样一个学生,为何校园内外,判若两人?盖其原因,缺少“人”的教育,心中并无真爱,遇到一点困难,内心就溃不成军。 大学教育,本来是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现在却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标。说好点,是培养出一些以“知识”为武器,为利益集团和自己谋利益的“砖家”;说差点,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和“人性”只有五毛钱的关系。 北大教授钱理群之所以能说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和北大和清华在“文革”结束之后,不同的教育理念所致。北大认为,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缺少独立思考的人;而清华觉得,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缺少专业的技术官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九十年代中国官场“清华帝国北大荒”的景象,让北大培养“独立思考的人”的教育理想,就象南门外的围墙,拆了建,建了拆,最终落入了培养“工具”的泥塘。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要知道人本身的价值,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在那里,往那里去? 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能什么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学会将心比心,认同和谅解别人的立场。一个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别人的死活,就像希特勒一样,很容易变成成极端分子;一个人没有立场,仅把大众的好恶做为归属,就是一个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学之中,这两种人正源源不绝地涌向社会,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对他们进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宣传各种规则,人的德性是在行为中间培养出来的。一位西方哲人说:“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成为正当的人,我们通过节制的行为成有节制的人,我们通过勇敢的行为成为勇敢的人”。 据报道,当大隅良典接到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在日本,很多的知名教授都亲自下实验室,亲自带着学生做实验,亲自复核数据,学生的德性就是老师这么带出来的。 在中国的大学里,像大隅良典这个级别的教授,很多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也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训斥学生等等。 大隅良典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喜欢跟人竞争,我没有自信能赢”。这句话后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持之以恒,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些都和技术无关,与一个人的精神相连,科学和技术的后面是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是余勇可贾、负重任走远道的精气神。 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知识和技术。显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太欢乐,太自以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