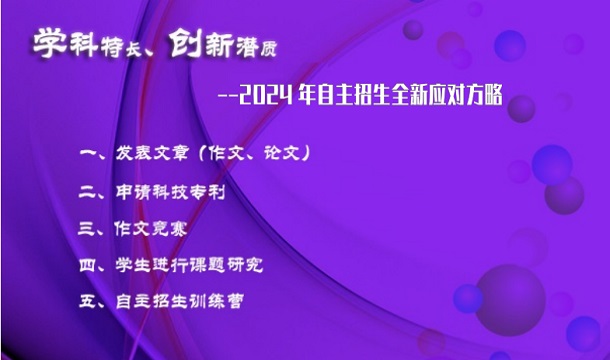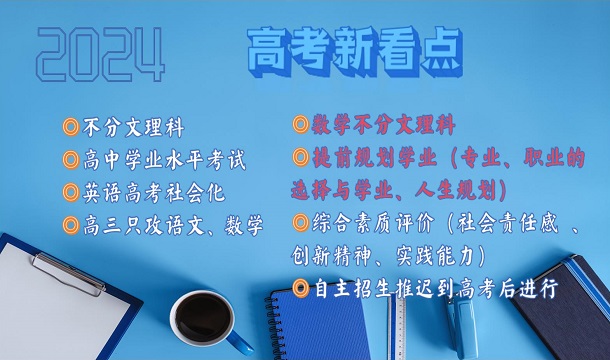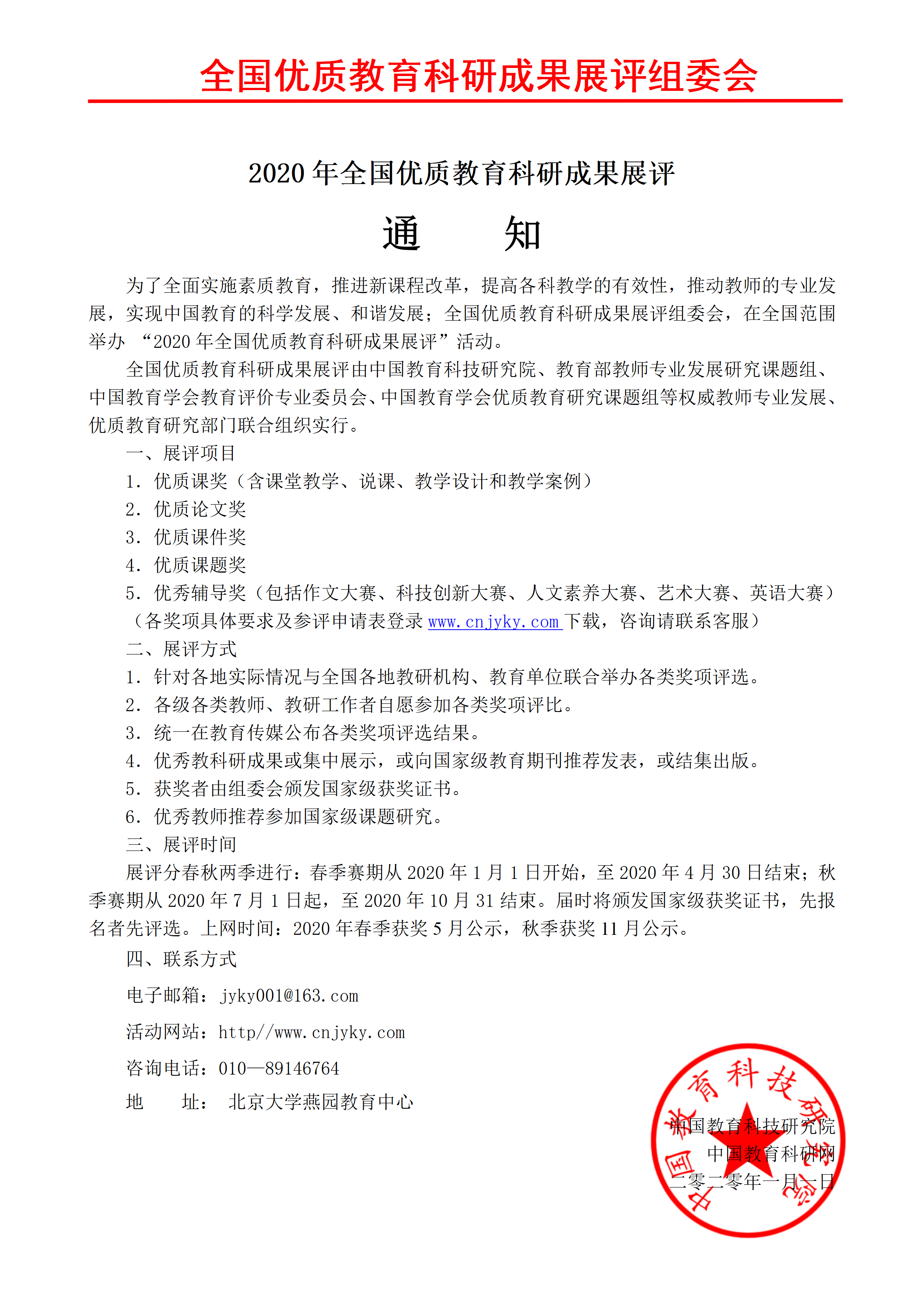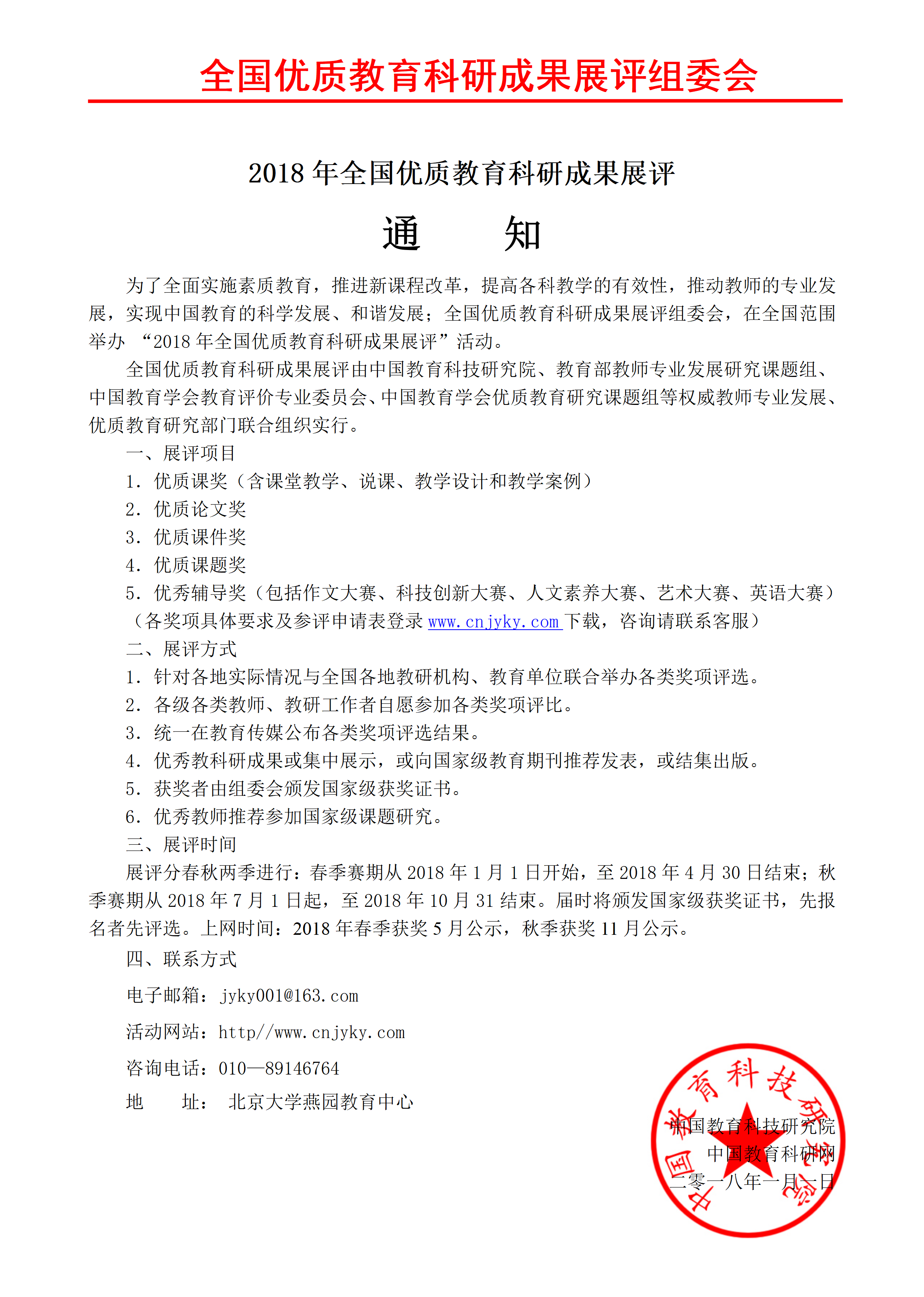| 从普及到传播,从信赖到理解 |
| 时间:2015-05-07 来源:田松 |
| 这个标题其实是抄来的。两个德国人编辑了一部书,叫做《在理解与信赖之间》,该书所讨论的就是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这个书名准确地抓住了人们对待科学的感情变化,也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之间的关键差异。 科普是科学普及的简称,它指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外所有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包括出版、展览、讲座等。在科普这个概念下,科学天然地具有正的形象,具有正确、高明、有效等正的含意,甚至拥有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有一个至今仍经常出现的词组“神圣的科学殿堂”,就表明了科学在日常话语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地位。在这种语境下,科学只能是人们崇拜、学习、遵从的对象,不能是批评、怀疑和亲近的对象。而人们所能够学习和遵从的当然是具体的科学知识。公众对于这些知识的态度用信赖一词来描述是恰如其分的。在某些时候,这种信赖甚至到了盲从乃至迷信的程度。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不理解科学的情况下,信赖科学。在对具体的科学原理不甚理解的情况下,信赖权威给出的结论。这种社会心理已经被广告商作为广告诉求点,比如那个经过了多少个博士、多少个硕士、多少个科学家进行了多少次实验的某某产品。农科站的小伙子推广科学种田,他只需要给农民讲清楚如何使用化肥、如何使用农药,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为什么使用化肥和农药,化肥和农药的作用原理如何,农民甚至不需要懂。在科学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农药和化肥已经具有正的价值。传统的科普往往是在这个背景上进行的。 科学的这种意识形态背景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主张科学是最高的价值判断,是最高的知识标准,甚至主张用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它文化活动。在社会实践层面,唯科学主义表现为技术主义,相信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技术具有天然的善的意义,任何一项技术成果都会激起人们的欢呼和颂扬。翻一翻当年的报纸,看看人们如何评价氟里昂的发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科学以及科学技术殿堂形象在20世纪遭到了全面的消解。一方面,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以及核冬天的可能性使科学技术的负的一面不庸置疑地摆在了公众面前;另一方面,20世纪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以及科学自身的发展都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不再代表绝对正确的真理,而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科学也并不天然地比人类其它的文化活动具有更高的价值。科学从神坛上降了下来,成为人们可以理解、怀疑乃至批判的对象。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应运而生。阿西莫夫对此有形象的表述:“你可以不做一个文学家,但是不妨碍你欣赏莎士比亚。同样,要欣赏科学,也不一定要做一个科学家。” 理解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了解一些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指对科学这种人类的认知和实践活动有整体性的理解。比如: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这种活动遵循什么样的法则,科学与人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科学与技术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固然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超越具体的科学知识。比如在一条街上,有一个鞋匠和一个车匠。鞋匠和车匠在闲暇时聊天。鞋匠说:我今天修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鞋,这个鞋是如何如何难修,我又是怎么怎么样把它修好的。在鞋匠的这个描述中,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修鞋知识。但是鞋匠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指望车匠能够拜他为师,跟他学修鞋。而车匠尽管不会修鞋,只会修车,但是它能够通过鞋匠的描述理解鞋匠的活动,理解他的喜怒哀乐。相反,传统的科普由于强调具体的科学知识,会把注意力放在讲述修鞋的具体步骤上。这就使不想改行学修鞋的人敬而远之。 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对具体知识的普及只是科学传播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制度化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播当然地要由学校教育完成。传统科普就是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学校教育无法分清界限,从而使自己主动地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当然,科学传播不仅在理念上与科普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传播手段上也与传统科普有所不同。相对于传统科普来说,科学传播更强调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科学传播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其预期受众是全体公众,而不仅仅是传统科普的“广大青少年”。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理解,打破科学事业与民众之间的藩篱,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科学前沿进展和基本科学知识等方面使公众对科学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科学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决定着我们的现在,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理解科学,了解科学和技术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了解它们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使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决策能力,而不是完全依赖少部分科学权威和技术专家的判断。 我们反对对科学的信赖,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科学的信任,而是因为我们更多地理解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