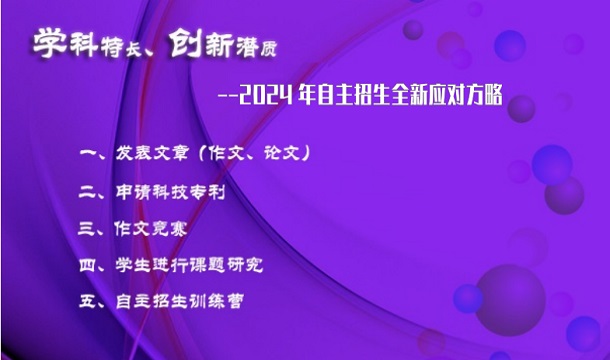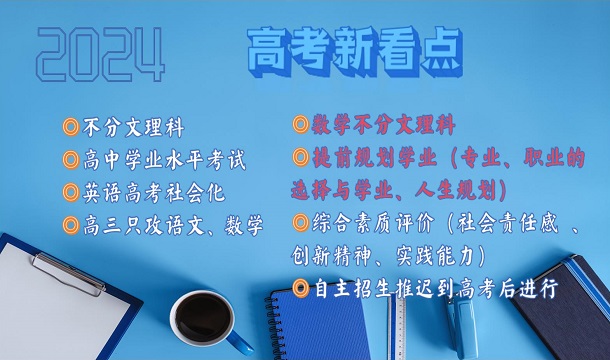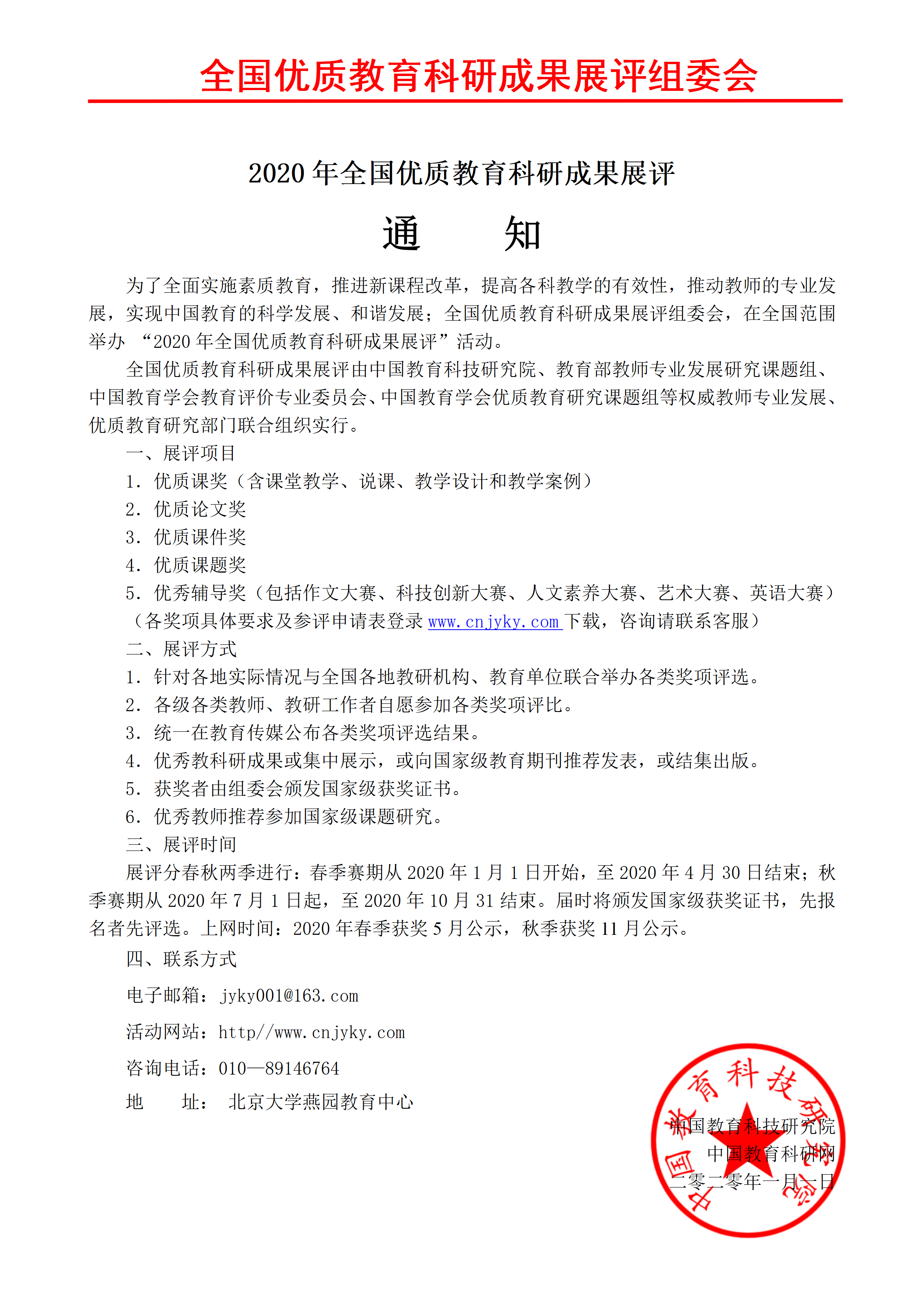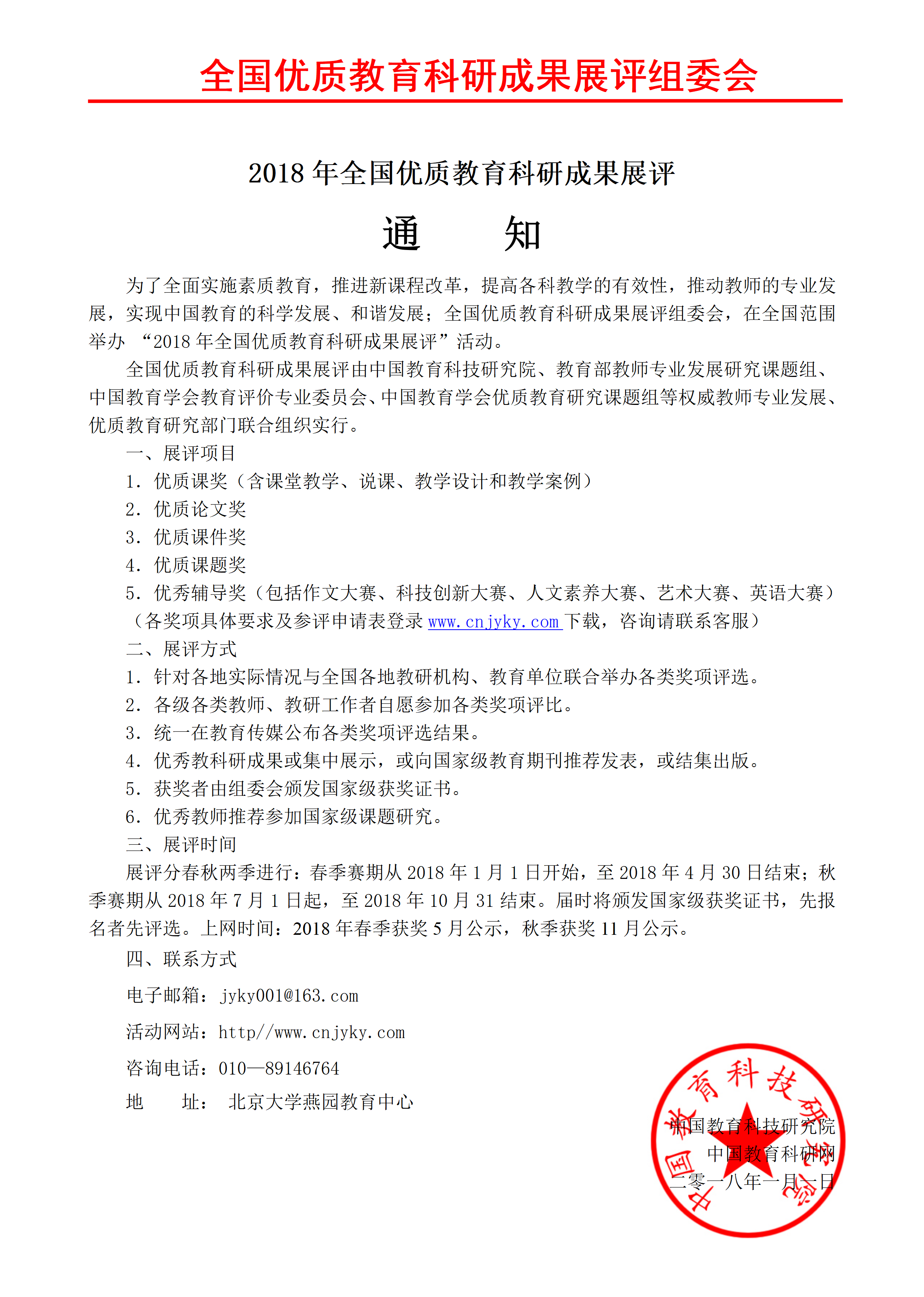| 凌宗伟:书院文化与现代教育 |
| 时间:2015-12-10 来源:凌宗伟 |
|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中,书院文化尽管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大的部分,但一直被某些群体视为固本培元的某种方式,而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 谈及书院文化,不少同仁或许会想到“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因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因学说论点不同,常起争论,故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于是有了朱、陆两派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其实质,无非为求个正宗与教主罢了。同样,今天以怎样的姿态看待各自的主张,既能坚守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又有兼容并蓄的胸怀,如何由论辩、争论转为对话,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量。 自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下的班级授课制的严重冲击,书院文化的影响似乎并没有达到历史的顶峰,但回过头来看在今天这个千疮百孔的教育生态和虚妄恣意的教育现场,很多人将救赎之道依然转向了传统的书院文化。并开始以星星之火之势,不断在国内生根、发展、壮大。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我国的书院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授受机构,更不是“技校”的代名词,而是一套完整的“成人教育”系统。当然,在外化的物质方面,书院主要有两大载体:人与书。“人”作为一切书院文化的主体,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人(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本身居于教育的中心位置,这和现代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是完全契合的。也即是说,不断是学科教学,还是德育、美育、体育,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健全“人”本身,为“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如此理念,虽然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一个积淀着历史一个引领着前卫,但这两者恰恰是殊途同归的。 书院的另一个载体即是“书”。这“书”,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书,因为书院的根本指向不是谋取功名利禄,而是启迪获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智慧的路径。更进一步说,这书可以是先人经历的结晶,也可以是必须从“行”中求的“无字之书”。不妨这样概括:一个“书”字,道尽了书院文化的全部意蕴。 书院文化的优势,在于去功利化、去绩效化、去市场化的将“人”和“书”天然的结合到了一起,从而生成某种生命意义上的“愿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传统书院大多具有以人为本,经世致用,自定教材,自由讲学的文化愿景。如何使这种无法物质化的“愿景”高度与现代的学校文化契合,其关键恐怕还在承认教育有其本然的规律,并按照该规律在现实的生态中慢慢还原、慢慢改良。 从“人”和“书”两个维度看,就书院文化的特质,我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就生长的“人”来说,他必须是高度“独立”的,尤其精神的高贵性和独立性,同时又具有“领袖”气质,能够指引和帮助其人芸芸众生过上更加美好和更加幸福的生活。当然它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拥众”,即经过自我影响力的辐射,可以慢慢形成一种效应,让更多的人转变人生方向,变得更加澄明和纯粹。 从“书”的角度看,一个有着良好的传统书院,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也就是能让人潜沉下来而不被打扰的环境),表现得非常的“闲适”和“散漫”(唯有如此,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做人做事的法门。)当然,这种封闭与散漫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不作阐述。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天天要开会,要接受评比和验收的教育生态中,讨论的书院的封闭与闲散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清代贵州兴义的道台刘官礼当年从血与火中走进了幽静而书香的笔山书院。为实现“文化天下”的理想,兴办了笔山书院。这亦公亦私的族学性质的学校,既成功地培植和壮大了其家族姻亲势力,又成为后来民国军政风云人物的摇篮。在与回教、洋教、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文化的对立冲突之中,以其影响,礼聘贤达。笔山书院在兴义地区传承了华夏文明。既有振兴地方教育之功,又有为中原文明在蛮荒之地夺取地盘的归化之功。 惠贞书院作为为一所特立独行,以“内知中国,外明世界”为宗旨,高扬书院精神的现代学校,它的节奏一定不会特别快的,是会在人文精神的引领下按教育应有的节奏做自己认定的事情的。如卢梭所说:“教育就是浪费时间”,她重要价值引领,而不是对“效率”“模式”等市场化的指标为追逐对象。同样,一所传承百年、生命力旺盛的书院,绝不是靠名次和分数坐稳天下,而是在“价值引领”和“自由选择”上做足文章,尤其是当今教育生态不断恶化,教育常识常备践踏的大背景中,她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有着一种寻找同道者“抱团取暖”的意识,因为正是抱团取暖,才可以使自己坚守信念、实践理想,让自己走得更好、更远。 在当下这样的教育生态中,书院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教育信仰的存在与坚守。但它也如同其它正常学校一样,永远需要处理好人、书、事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立人为命业,读书为抓手,在实践中明理,在传承与批判中前行。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在倡导“互联网+教育”的今天,无论在理念还是形式上,在坚守与传承的同时,还有一个变革与创新的问题。正如《易经》的“易”一样,坚守和变革,传承与创新都要高度统一在教育规律和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坚守现代学校文化的文明与共识,舍却不合时宜甚至谬误的东西;变革那些与时代发展潮流格格不入,甚至阻碍社会进步的那些庸俗腐朽的东西。 重庆的聚奎中学的前生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建成的聚奎书院。这所“川东名校”在20世纪初就是以办学质量高而闻名巴蜀。民国时期冯玉祥、陈独秀、梁漱溟、文幼章等曾到过那里讲学,学校为当代中国培养了如周光召、邓若曾、邓焕曾、吴芳吉等一大批社会精英。这些年热火的“翻转课堂”这一概念和教学变革就是从聚奎中学开始走入中国大陆基础教育的。 还有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传统的书院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社区文化衔接打通的问题。 江苏常熟的石梅小学坐落于虞山东南麓,梁昭明太子读书台旁。其前身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粮储道杨本植所建的“游文书院”。两代帝师翁同和曾就读于此。这所小学自2001年开始将地方高校、尚湖风景区、宝岩生态园、交警中队、居委会、军营等单位作为石梅学生社会实践的基地。通过去博物馆找想象力系列活动、爬山课、美术馆小小毕加索现场课、曾赵园里的语文课、翁同龢彩衣堂里话校友等活动打破了学习和生活的界限,架起了学校和社会的“桥梁”,密切了师生的交往,为学生自由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 江苏徐州铜山县的汉王小学甚至用他们的理念与行动影响了整个汉王镇的社区文化。 学校教育对社会的反哺功能,从杜威开始,就得到了教育学者的高度重视,学校即社会成了一种教育原则被确定下来,之后的陶行知等人无不践行着这一规则。以书院精神办学,不仅要“内知中国,外明世界”,还须明白,与其“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唯有如此,“立人”的宗旨才有可能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