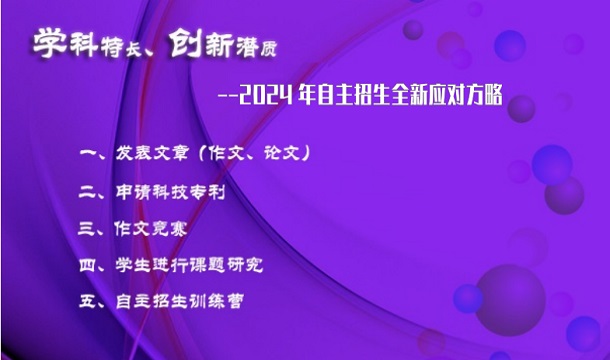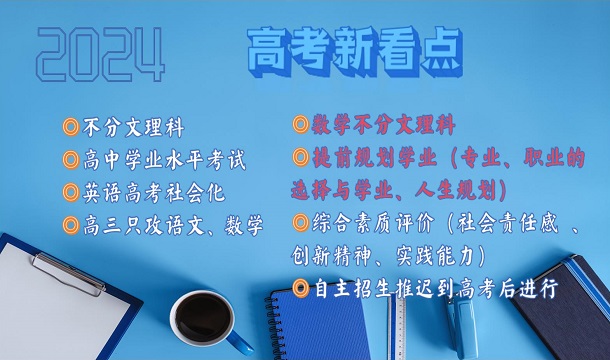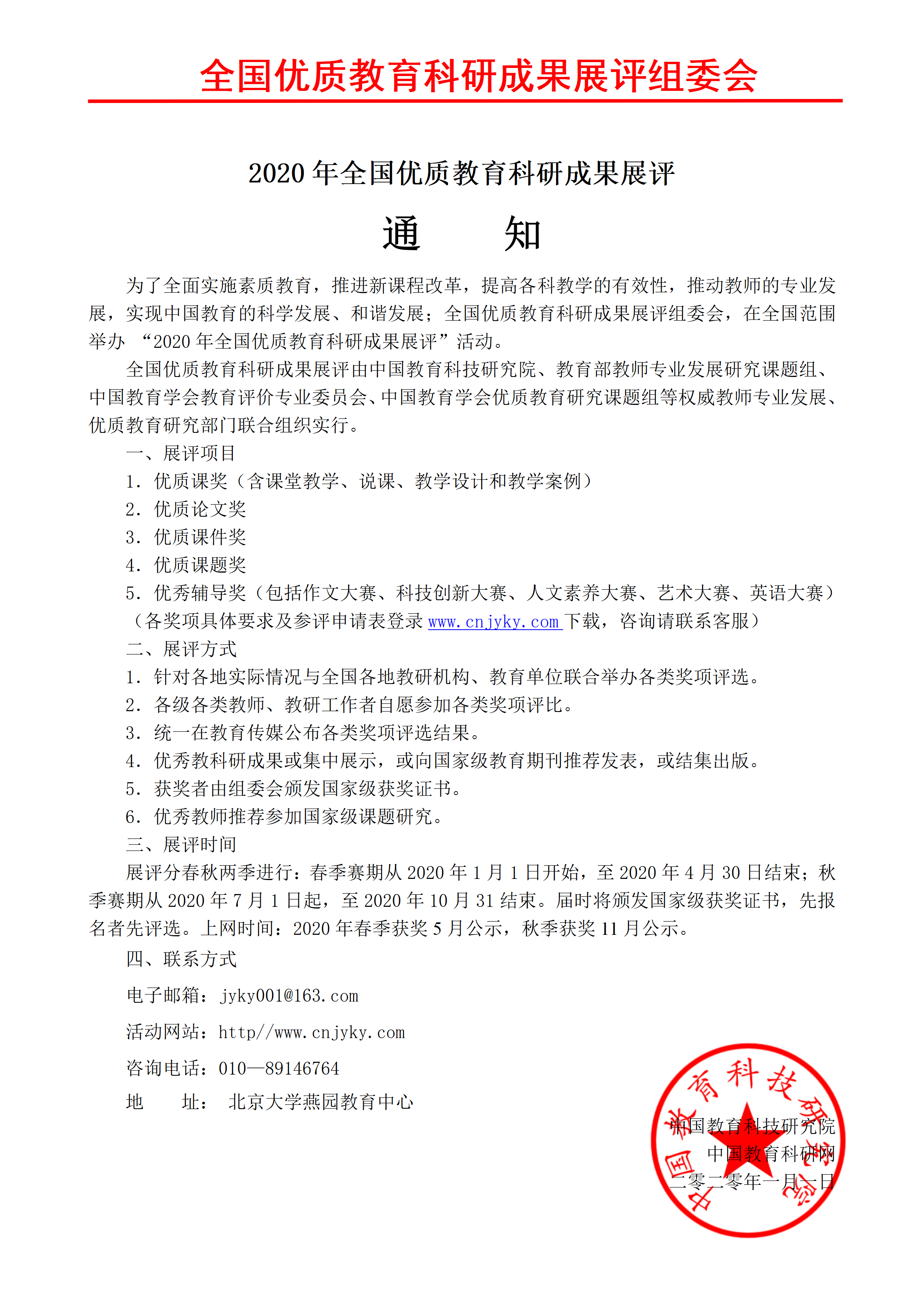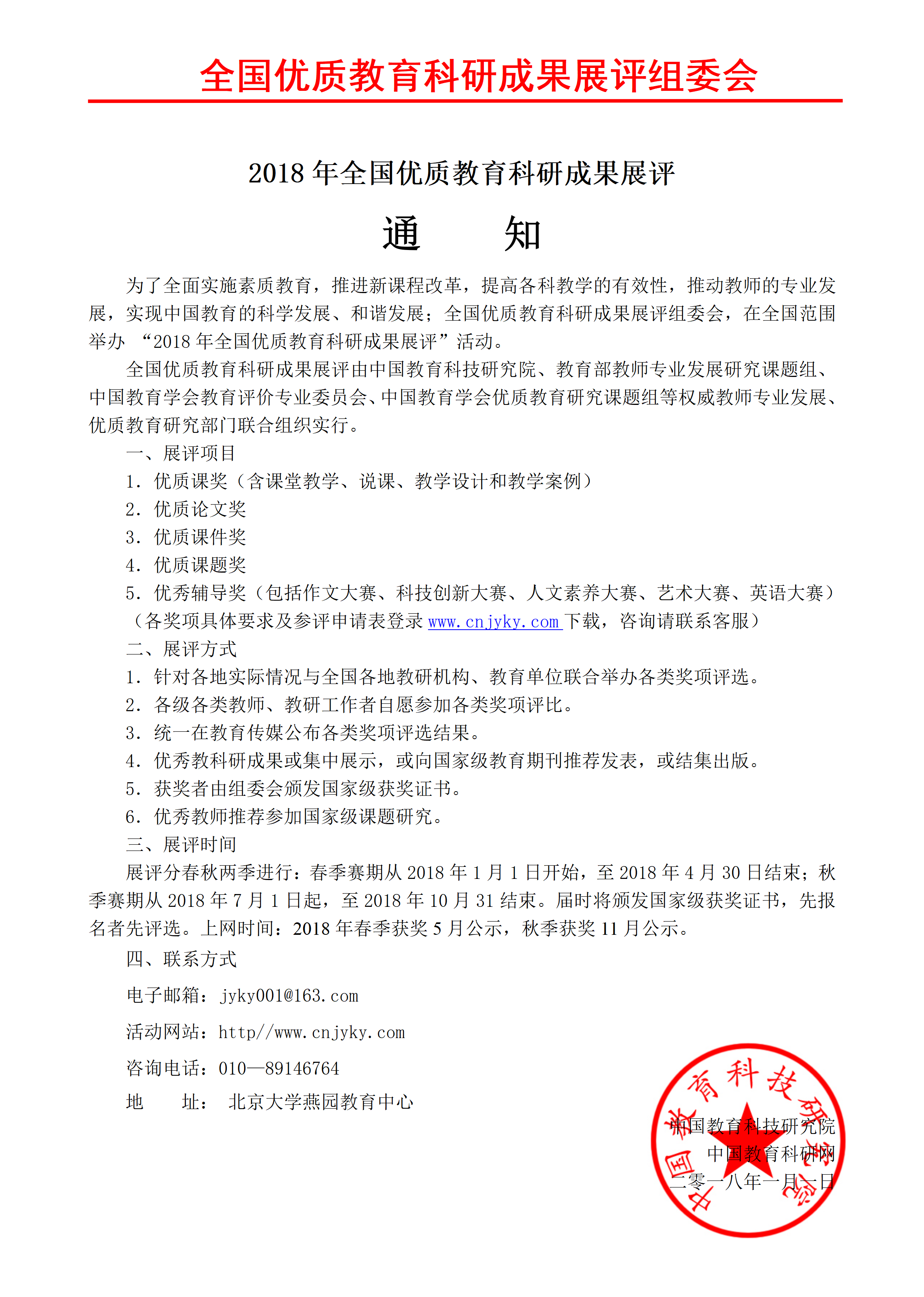| 饶毅:科学的病出在文化上 |
| 时间:2016-08-01 来源:admin |
 饶毅 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与西北大学,2007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昨天,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这是中国科学界迄今所获的最高奖项,国人为之欢呼雀跃,科学也再次受到异乎寻常的瞩目。 素来关注科学与科学精神发展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饶毅,曾著有《饶议科学》一书,但他对科学远不止于“议”,还直接参与了多项科技体制改革。这个过程让饶毅深有感触:当前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科学精神要在文化上深入人心。 重温科学史,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不再沉醉于虚构的辉煌中 ■科学和技术,两者虽密切联系,却区别甚大 ■“中国古代科学先进”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相比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稍好些,但总体上也是落后于西方的。但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将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体。 饶毅: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而技术是人类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 科学和技术,两者虽密切联系,却区别甚大。科学主要解决理论问题,技术主要解决实际问题。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发现自然界中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并建立理论把事实与现象联系起来。技术常常是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技术倒逼理论的情况。 科学主要是和未知的领域打交道,其进展,尤其是重大的突破,是难以预料的;技术一般是在理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作,可以做规划。 记者:您的“落后说”,显然与“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主流”说法背道而驰。 饶毅:文化和科学史显示,中国古代在军事谋略、诗词歌赋等方面都很有创造性,也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些原创技术,但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落后于古希腊起源的西方科学。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广为传播,一些国人出于良好的愿望,把它引进国内,但它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记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近来颇受关注的一部关于古代物质文化的通史,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领先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技术。 饶毅:列举个案并不能证明整体上的先进,而且,技术的先进和科学的先进是两回事。 比如,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了《几何原本》,这样严密的系统科学在200年前的中国也还不存在。《几何原本》的译者之一徐光启,在比 较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意思是,我们的运算方法与《几何原本》略同,但完全 没有《几何原本》所阐述的那些原理,让学习的人只会这么算,却不晓得为什么要这么算。 记者: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加强自我认知,这样的认知很清醒,但却可能引发部分国人的心理不适。 饶毅:重温我们的科学史,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不再沉醉于虚构的辉煌中。如果说以前我们是把“李约瑟假说”当成一种自我鼓励,那么,到了今天还这样认为的话,就是自我麻痹了。 科学精神缺乏,是我们文化中的重大缺陷 ■好奇心的缺乏,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强 ■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粉丝无数,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 记者: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儒学创始人孔子承认人的认知存在局限性。而作为现代科学与文明诞生基础的基督教,则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比较而言,难道不是中国的土壤更适合科学生长吗? 饶毅:科学的发生是件很奇特的事情。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科学是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的科学居然能够发生,并且得到发展,这不是奇迹吗?很多文化里都没有萌生科学,在中国古代没有萌生科学也是正常的。 每个民族都有一些人在智力上有所追求。西方的这些人更多去研究自然科学了,而中国的这些人更多去创作诗词歌赋。最初,你不能说哪条路是对的,它们只是不同的路;但到了今天,不同的道路选择带来的结果是十分不同的。 记者:因此,与其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萌生科学,不如讨论中国科学传统的缺乏给今天带来的影响更有意义。 饶毅:是的。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贯穿于科学活动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我这么说,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科学精神包含了很多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比如,尊重事实。刚刚提到的“李约瑟假说”,很动听,但不是事实, 我们就不能听。再如,双方争论,彼此应该认真听取、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看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部分。这是科学精神应有的理性和包容。当然,包容不是良莠不 分,不是一团和气,而是通过理性的讨论和深究,逼近真理。 记者:您如何透视我们科学精神不足背后的原因? 饶毅: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足有关。中国人不喜欢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喜欢探求人与人的关系。 英国早期有一批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就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做研究。力学定律、光学原理都不能直接生产出产品,也不能让科学家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这样的科学有很强的“后发力”,日后帮助英国强大了起来。 科学对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至关重要;瑞士是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却有21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国家都在科学领域进行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而不仅仅是发展实用技术。 记者:纯粹而不功利的好奇心,最后足以演变成为一种发展的巨大力量。 饶毅:好奇心的缺乏,可能直接导致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不强。假如我们对世界不好奇,不从事超前的、根本性的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可能总是落在为别人生产的层次上,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即使耀眼,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尊重。 科学有时是一条寂寞之路,特别在初期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在中国古代,诗作得好,可以收获很多粉丝,而鲜有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可以说,这种观念上的褊狭或多或少还在今天留有痕迹。 记者:对科学葆有多少热情与敬意,直接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生态。 饶毅:近代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科学书籍,同时建起西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但是,因为科学传统的缺乏,教育方式的现代化一时难以带来观念的现代化。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曾经抱怨说,很多人读北大,就是为了读商科和法科,为了发财。而今天,我们时常在喟叹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青少年似乎日益青睐能赚钱的职业,而对科学的热情却越来越少。 我们遇到问题,常常抱怨体制和机制,却对文化上的根源挖掘不深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限制了科学精神的培植与滋长 ■很关键的一点是,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成利益制度 记者: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民族的科学精神,让发生于过去的缺席,不再成为未来的缺憾? 饶毅:你说到文化的土壤,这个很对。我们遇到问题,常常抱怨体制和机制,却对文化上的根源挖掘不深。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科学精神不仅没有在文化上深入人心,而且,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限制了科学精神的培植与滋长。比如,在科学界,迄今未能解决创新需要冒尖的文化与我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冲突;在科学界以外,不科学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不时会冒出来。 记者:具体表现为什么? 饶毅:首当其冲的就是科学的评价体系。 上世纪后半叶,评价科技作品还是以大家坐下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大家尽力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但由于当下人与人之间互信度不够,以及腐败对中国科学界 某种程度上的侵袭,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量化指标。一个个指标列下来,评审员要做的事就是数数、统计。数数总不会数错吧?这样的评审,看上 去客观,实际是不负责,此外还导致了用处不大、质量不高的论文的泛滥。 举个例子说,现在自然科学基金会甚至规定评委之间不可以交流、讨论。因为评审机构发现,以前设立的讨论环节竟成为了某些人拉选票、搞串联的契机。 记者:量化的指标与硬性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奏效,相反,人们对科学评价体系越来越心生疑窦。比如院士制度,就曾一度让很多人质疑。 饶毅: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成利益制度。如果当上院士,就有特别的待遇,掌握评审项目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就会导致有些人削尖了脑袋想当院士。 还有一点我总觉得比较可笑,那就是开会院士坐主席台。其实在很多国家,院士该排队还得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不设主席台,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规规矩矩坐在台下。 记者:如何防止院士评审制度从荣誉制度异化为利益制度? 饶毅:院士制度是国家科研评价体系的“塔尖”,具有风向标作用。我们应该让院士的头衔回归到一种荣誉的表彰,而且仅是表彰一个阶段的原创性工作。曾有一位 美国科学院院士,刚刚因为多年前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却被资助他的某家研究所告知,他不能继续得到该所的资助,因为他近几年的工作做得不好。显然,这样的 事情很难发生在中国的院士身上。 既要去利益化,又要坚持原创性贡献为评审核心依据,才能让院士制度与院士评审回归科学的本义。 在科学上一定要允许、支持争议 ■用总分衡量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公平 ■有思想、有内容、有道理地“说”,常常就是很重要的“做” 记者: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创新力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在现实中演绎的? 饶毅: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某大学曾有三位青年科学家竞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结果,最优秀的人在第一轮函评中就出局了。经过第二轮审,差的那个也被淘汰了,走到最后的是那个中等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时有发生。评委来自各家单位,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先砍掉最好的?因为淘汰别人单位最好的,自己单位中不溜秋的就有了胜出的希望。如果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我们的社会也会变成一个中不溜秋的社会,优秀就被“有效”地扼杀了。 记者:一个中不溜秋的社会,是难有创新涌动的。 饶毅:培养创造性人才关键要在四个方面做努力:发现特色、保护争议、支持青年、坚持理性。 发现特色是前提。我们的教育是以总分选学生,但有些人就是偏科,总分没戏,却在某一方面有天赋。而这种四平八稳的总分选拔制,是发现不了特色人才的。如果不懂发现特色,那么当年就出不了孟德尔,也出不了华罗庚、钱锺书。用总分衡量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公平。 保护争议也一样,越是超前性的工作,越有可能引发争议,而中庸文化是希望争议越少越好,最好没有,争议没有了,突破性发现的概率也就降低了。所以,在科学上一定要允许、支持争议。 支持青年的意思是说,不是谁年纪大谁就是权威,不是权威的观点就不能质疑、不能讨论、不能反对。如果什么都不能,年轻人怎么出得来? 而实现前面这三点,都需要以坚持理性为保障,不然就会乱套。 记者:所以您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体制,而是文化。文化不变,体制怎么改都没用。多年来您持续发声,今年9月,还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这些是否都可视为一种试图改变文化的努力? 饶毅:是的,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就是希望能够在文化上带来一点点改变,让科学精神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在努力。 有时候,“说”就是一种“做”,有思想、有内容、有道理地“说”,常常就是很重要的“做”。 (实习生项来婷对此文亦有贡献)(原标题:科学的病,出在文化上——对话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